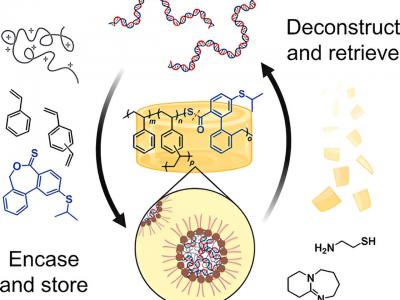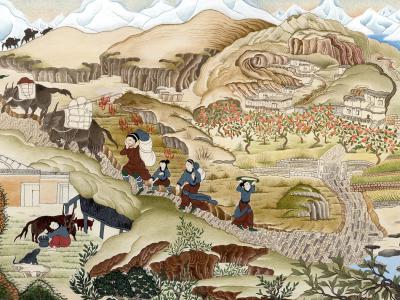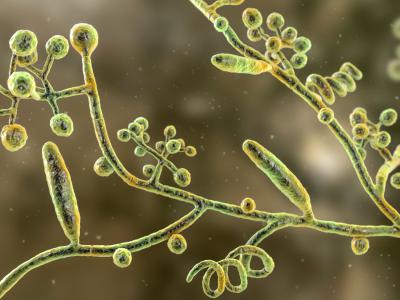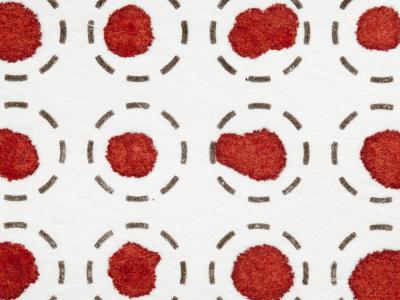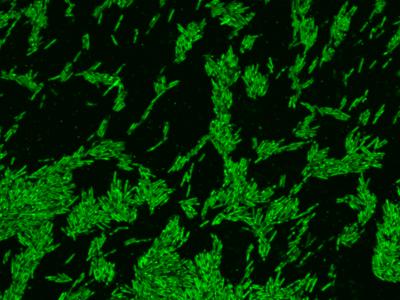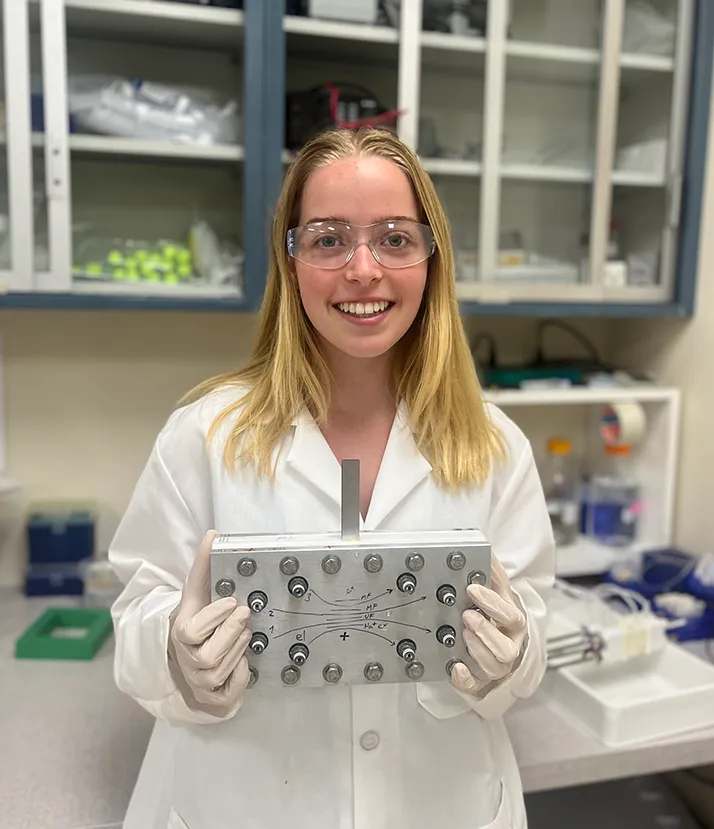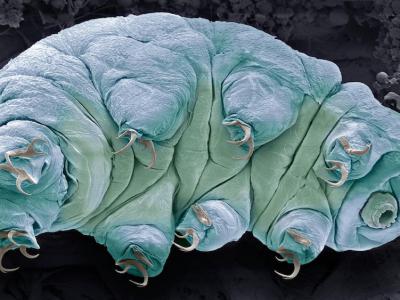人类为何爱哭泣?
我们是唯一会因为情感而流泪的动物。这是为什么?又是大脑中的哪些部分控制着我们哭泣的冲动?在《人类为何喜欢哭泣》一书中,迈克尔·特林布尔从神经科学、艺术和进化等方面对答案进行了探索。
他的基本论点是,人类大脑中有一套神经系统,对情感刺激,特别是对悲剧,作出选择性反应。他的意思是说,个人对失去的体验与语言和文化协同进化,导致———至少是促成———同名艺术形式的诞生,即把丧失和痛苦作为人性非常重要的方面。
特林布尔仔细研究了神经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试图解释人类是如何以及何时认识到生命的悲剧性质,并因为情感的波动而哭泣,甚至从悲剧引发的哭泣中获得一种快感,他称之为“悲伤的喜悦”。
他大胆地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日神、酒神秉性概念入手,研究了这两个概念如何分别对应视觉艺术和音乐艺术。特林布尔接着以此比喻心理过程根植于神经解剖学准则和进化准则:日神秉性比喻支撑意识推理的大脑回路;酒神秉性则比喻控制我们情感且进化时间更早的皮质下回路。
在经过对哭泣文献的一番回顾,并对假定存在的情感神经电路进行一番详细的评价后,他的笔端转而探索情感哭泣可能的进化方式。文章从婴儿的嚎哭开始,婴儿的嚎哭与其他动物的悲号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我们从一出生就会随时关注母亲的面部。从而开启我们对面部以及其上变幻多端情绪的终生不渝的兴趣。出生后不久,眼泪就开始伴随着哭泣流下来,于是,标志着我们“痛苦及要求抚养和帮助”的系统诞生了。
特林布尔用悲剧来论证神经和社会现象可能协同进化,从而产生我们偶尔的宣泄性眼泪。也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哭泣能够提供某种慰藉的时候,一旦需要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地诱发这种感受。
他说,我们的大脑形成了“一种激发与安抚的特殊结合体”来应对悲剧。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可能诱发悲伤的喜悦眼泪,这两个区域对共情感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特林布尔断定,同时也是更加原始的、与恐惧和强烈情感关联的杏仁核体的激活减弱才造成悲剧诱发出共情和亲昵的感情。
参考消息 (作者纽约瓦萨尔学院心理学教授伦道夫·科尼利厄斯)